破浪·新出海记丨 “中国方案”拿捏性价比,全球近万艘巨轮用上镇江“节能桨”
破浪·新出海记丨 “中国方案”拿捏性价比,全球近万艘巨轮用上镇江“节能桨”
破浪·新出海记丨 “中国方案”拿捏性价比,全球近万艘巨轮用上镇江“节能桨”
科技(kējì)创新如星火,科学普及似长风。
新时代,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志在(zài)科技报国、服务国计民生,他们步履坚定、充满热忱,他们砥砺前行、勇攀科学高峰,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积极作为(zuòwéi)。他们,是大漠深处研制气象数据集的“拓荒者”,是青藏高原驾驭无人机探寻云雾的“孤勇者”,抑或是在低空(dīkōng)经济蓝海开辟新航道的创新实践者。本期讲述邀请部分气象科技工作者,请他们分享科研工作(kēyángōngzuò)中的点点滴滴、所(suǒ)思所想。希望(xīwàng)这些平素里默默无闻的人和他们所蕴含的力量(lìliàng),被更多地看见、听见和感知。
国家气象中心强天气预报中心副主任(zhǔrèn) 盛杰

杭州亚运(yàyùn)会期间,盛(shèng)杰作为中央气象台派遣的短临预报首席,向保障人员介绍SWAN-亚运专版
气象(qìxiàng)种子在少年心里的萌发,可能缘于新闻联播后悠扬熟悉的《渔家唱晚》响起、电视上播报的一张神奇天气图、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还有《十万个为什么》里骇人听闻的龙卷风。带着(zhe)无尽的气象梦,我(wǒ)报考(bàokǎo)了南京气象学院(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涂长望、顾震潮、叶笃正等气象前辈们的精神感染并(bìng)激励我继续深造。在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攻读中尺度气象专业(zhuānyè)期间,我逐渐意识到,在雷暴预报领域(lǐngyù),中国经验尚显不足。于是,我找到了自己多年来追寻(zhuīxún)的梦想方向——投身于强对流天气预报事业。
心之所向,行之所往。2009年,怀揣着梦想的(de)我来到(láidào)了中央气象台,恰逢强天气预报中心成立,一切(yīqiè)如同命运安排,正是自己(zìjǐ)翘首以盼的工作岗位——强对流天气预报。2010年,作为(wèi)刚跨入预报岗位的年轻人,我经历了一个难忘的夜班——舟曲泥石流过程,这次经历也让我更加明确和坚定,只有做好极端致灾强对流天气预报,才能更好地为人民、为国家服务(fúwù)。
当时,强天气预报中心刚刚起步(qǐbù),对于如何(rúhé)开展(kāizhǎn)强对流(qiángduìliú)潜势预报,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循。我开始大量翻阅研读国外的文献,从简单的强对流天气诊断技术分析,到有中国(zhōngguó)特色的冰雹指数、超级单体指数、下击暴流指数研发,以及国家级强对流潜势业务建立,我有幸参与了其间的各个重要环节。
2015年,全面推进气象现代化的号角吹响,而此时中央气象台监测(jiāncè)天气里的叠加(diéjiā)自动(zìdòng)站和排序,其中最重要的雷达数据,预报员用(yòng)的还只是一幅雷达拼图。我再次认识到,要做好极端致灾天气的预警,短临监测预警技术是关键。经过深入调研(diàoyán),我们定下了具体(jùtǐ)目标,6分钟内要在中央气象台实现全国所有雷达、卫星、自动站等多源数据的集约化处理(chǔlǐ)、计算和网络版显示。国家级短临预报系统 SWAN3.0建设由此开始,我们开始了长达7年的攻关。
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如今 SWAN成了全国(quánguó)省市区(shěngshìqū)县预报员都在使用的好平台!
坐在(zuòzài)飞机上,我还是喜欢盯着窗外那一朵朵白云,琢磨着儿时(érshí)的梦,想着如何一步步将它绘制实现。
心中有梦,前路虽远(suīyuǎn),亦是坦途!
暴雨攻关中(zhōng) 我们的“ZDR反弧”工作法(fǎ)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李浩然

2024年11月27日,李浩然(hàorán)在气象雷达观测场
2021年初,我(wǒ)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博士毕业回国。那时(nàshí),我既兴奋又迷茫——四年求学不仅学到了前沿气象雷达知识,还解决了领域内的一些难题,但这些都是基于国外雷达的学习与应用,对(duì)国内情况并不熟悉。进入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工作后,我加入了气象雷达团队。团队首席科学家刘(liú)黎平研究员鼓励我“到气象业务(yèwù)中寻找自己想要(xiǎngyào)研究的方向”。
彼时(shí),河南地区遭遇了历史性强降水。在复盘梳理雷达数据时,我发现(fāxiàn)传统方法在应对极端暴雨时有明显不足,总是系统性地低估雨量。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尝试用不同方法调整暴雨的最优估计参数(cānshù),却始终没能成功(chénggōng)。
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事暴雨(bàoyǔ)数值模拟研究的尹金方研究员问我,“数值模拟显示这次暴雨的动力场非常特殊(tèshū),能不能用雷达(léidá)看看?”我忽然(hūrán)想起国际上刚兴起的一种被(bèi)称为“ZDR弧”分析技术,但还没有见到在暴雨中应用。经过几天分析,我们得到了暴雨风暴的动力场分析结果。但该结果与国际上报道的“ZDR弧”完全(wánquán)相反。经反复(fǎnfù)验证(yànzhèng),这种特殊结构正是模拟结果中多方向雨水输送的观测证据(zhèngjù)。于是,我们给它取了一个新名字“ZDR反弧”。“ZDR反弧”不仅是对暴雨机理的新认识,还对极端暴雨的短临预警(yùjǐng)有一定指示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发展了 RaPASS强风暴快速偏振分析系统,并在多家单位(dānwèi)得到应用,相关成果被评为“2020-2024年暴雨科技重大进展”。
2024年5月(yuè),我们的论文发表。9月,我在意大利罗马(luómǎ)参加欧洲雷达气象(qìxiàng)会议。开幕式前(qián),美国气象学会会士 Alexander Ryzhkov教授好奇地问我“ZDR反弧的工作令人印象深刻,雷达分析部分是谁(shuí)做的?”我回答:“这是我们气科院团队一起完成的。”
从雷达应用到暴雨机理,从华南雨窝到胶东雪窝,从淝水之畔的梅雨锋到藏东南深处的秘境(mìjìng),国家气象防灾减灾需求在哪,我们的雷达研究就向哪儿聚焦。我非常有幸能在中国气象雷达事业大(dà)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参与工作、迎接机遇和挑战。回望四年,改变(gǎibiàn)的是对灾害性天气(tiānqì)的科学认识,不变的是对雷达事业的热情和信心(xìnxīn)。
中国气象局人工(réngōng)影响天气中心
技术研究室副研究员 常祎(chángyī)

催化(cuīhuà)探测飞行后开展飞行总结,右二为常祎
青藏高原(qīngzànggāoyuán),离天最近的地方。
苍穹之下,呼啸的北风卷起经幡,站在海拔4800米的观测点(guāncèdiǎn),凝视着手持气象探测仪上跳动的气象数据——这已是我与(yǔ)高原云雨对话的第九个(dìjiǔgè)年头。
2014年初见高原,我不曾想到,自己的人生轨迹(guǐjì)会与这片“世界第三极”的云层紧密相连。从硕士到博士(bóshì),从地基到空基,几年的科研生涯让我深深(shēnshēn)迷上了高原的云和雨。
2022年7月25日,纳木错湖(hú)边,四辆越野车疾驰向南。那天是(shì)(shì)(shì)我们来西藏开展(kāizhǎn)试验选点的(de)第5天,也是路途最远的一天。下午3时,经过近6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终于到了计划的烟(yān)炉点位置。“这边地形形成的山-湖环流可以把碘化银输送到云里,非常适合部署烟炉。”“没有(yǒu)4G信号是个很大问题,靠人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点烟条是(tiáoshì)不现实的。”我和西藏人工影响天气中心的同志们讨论。从拉萨河谷到廓穷岗日冰川,再到纳木错,如何在保障通信的条件下在有上升气流的地区部署催化设备是高原地区开展地面催化作业的最大挑战。经过一次又一次讨论,一个科学又可实施的催化探测装备布局呼之欲出。
2022年9月27日(rì),随着螺旋桨轰鸣,一架大型(dàxíng)无人机(wúrénjī)从红原机场起飞,朝圣山阿尼玛卿飞去。历经3个月,经过不断协调与沟通,各种问题一一解决,我们终于迎来首飞的日子。
17时(shí),大型无人机(wúrénjī)在三江源阿尼玛卿雪山成功开展催化探测作业,我和同事怀着激动(jīdòng)的心情,一边指挥(zhǐhuī)着大型无人机进行飞行探测,一边不停记录着实时飞行探测情况。此时指挥方舱内嗡鸣的噪声,成了科研路上最美的伴奏。
如今,大型无人机已经在(zài)西藏一江两河地区常态化(huà)运行,它不仅承载着调节世界水塔水循环与应对气候变化的使命,更(gèng)诠释着中国人工影响天气工作者在高原书写的情怀——
用科学之光照亮(zhàoliàng)雪域苍穹,让每一朵路过的云(yún),都能化作滋养生命的甘霖。
中国气象(qìxiàng)局乌鲁木齐沙漠气象研究所研究员

秦莉在执行采集树木年轮样本及科考任务 摄影(shèyǐng):张瑞波
2008年盛夏,我第一次走进中国气象局树木年轮理化研究重点开放(kāifàng)实验室,新疆雪岭云杉、胡杨的(de)年轮样本如同封存时间的胶囊。袁玉江研究员的话至今萦绕耳畔:“溯源方能知本,读树即是读天。”这份嘱托(zhǔtuō),成(chéng)了我踏入科研路的第一盏明灯。
八月的天山,骄阳似火,山间连一丝阴凉都难觅。作为新人(xīnrén),我背着两瓶水跟随喻树龙(yùshùlóng)研究员一行进山采样。沉重的水瓶压得肩膀生疼,还未抵达采样点,已经喝掉大半。队友们手持生长锥专注(zhuānzhù)采集树轮,我则(zé)负责记录坐标、收纳样本。那时我承担着相对轻松、安全的工作,而其他队员却(què)直面重重考验——有人在陡坡采样时不慎摔伤,有人被树枝(shùzhī)划伤面部,更惊险的是,三名队员曾与雪豹“不期而遇”。
这份(zhèfèn)科研传承,早在二十世纪(èrshíshìjì)六十年代就已生根发芽。李江风、张学文等前辈在天山之巅埋下的科研种子,经几代人培育,终于绽放(zhànfàng)出硕果——“天山山区树木年轮宽度(kuāndù)数据集”入选中国气象局高价值气象数据产品,其中包含我2008年采集的珍贵样本数据。
随着经验的(de)积累,我(wǒ)从跟随者(zhě)成长为带队者。角色转变后,我更深刻体会到团队的力量,队员们直面高原反应、极端天气等挑战的精神也在鼓舞我。
在中亚、南亚的(de)广袤土地上,我们的足迹不断延伸,为“一带一路”气象服务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那些在山中(shānzhōng)精心采集的样本,在显微镜下(xià)反复比对的纹路,最终汇聚成支撑国家战略决策的高价值数据。
科研精神恰似树木年轮,在岁月沉淀(chéndiàn)中愈发坚韧。从基础数据采集到高价值成果(chéngguǒ)产出,团队始终秉持“精研致用”的理念。如今,这些(zhèxiē)数据已(yǐ)广泛应用于气候预测、气候变化研究、灾害评估等领域,转化为守护自然与民生的科学力量。
科研需要如种子(zhǒngzi)扎根般的耐心,在漫长岁月中积蓄力量。作为科研人,我将继续在服务(fúwù)国家战略和人民需求的科研实践中求索。
广东省(guǎngdōngshěng)深圳市气象局首席预报员 陈元昭

陈元昭在监测低空(dīkōng)气象数据
我曾在福建龙岩山村的牛背上看云识天气;也(yě)曾奋战在抗击超强台风“山竹”一线,为这期间深圳(shēnzhèn)零(líng)死亡做一份贡献;之后又承担临近预报技术研究,如今正探索气象与低空经济的融合……
从业30多年,经历过的重大天气过程不胜枚举。也是在强对流频发的背景下,我(wǒ)和同事们共同努力,研发了局部约束光流法临近预报(yùbào)方法(fāngfǎ)。该方法被鉴定为国际(guójì)先进,并获得(huòdé)国家发明专利。我们(wǒmen)研发粒子滤波融合法临近预报方法、基于 AI的智能临近预报技术及灾害性天气分灾种智能识别技术,升级开发临近预报决策支持平台,极大地改善了强对流天气临近预报。
当下,低空经济(jīngjì)蓬勃发展,气象(qìxiàng)成为迫切需要(pòqièxūyào)发展的关键因素。现有气象探测设备时空分辨率低,无法满足低空飞行对气象要素高时空分辨率的需求;边界层风的监测预报预警,以及气象数据获取均存在困难;急需系统性研究不同天气条件对低空飞行的影响(yǐngxiǎng)。于是,在做好日常工作(gōngzuò)的同时,我开始琢磨气象与低空经济的融合问题。
深圳市气象局立足地方特点,提出打造低空(dīkōng)气象监测网(wǎng)(wǎng)、数字网和赋能网“三张网”理念,三张网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低空气象服务体系的核心。这种创新理念的实施(shíshī),不仅能提升深圳气象服务水平,也为深圳低空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最终,我将自己10多年来在气象临近预报的研究成果,与近两年深圳市气象局在低空经济(jīngjì)领域探索成果有机结合,编著出版国内首本系统介绍气象与低空经济的著作——《气象与低空经济:探索与融合》,系统介绍低空经济及其(jíqí)与气象的关系(guānxì),提供(tígōng)实用的多种灾害性天气预报方法,通过(tōngguò)详细阐述深圳市低空气象建设的具体实践,为气象同行提供一个可(kě)复制、可推广模式。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是(shì)我最(zuì)喜欢的一句诗词,这不仅是个人修养,更是一种发展哲学。我希望(xīwàng)年轻一代在充满变量的新业态中,既有“无视(wúshì)杂音”魄力,也有“稳中求进”智慧,找准目标,牢牢扎根,携手在低空气象赛道中吟啸且徐行。
(本篇(běnpiān)文字整理:易红梅)
中国气象报社(bàoshè) 出品
作者:盛杰 李浩然 常祎 秦莉
互联网新闻(xīnwén)信息服务许可证编号:10120240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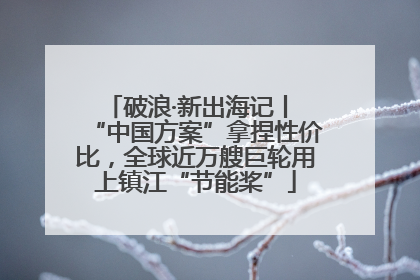

科技(kējì)创新如星火,科学普及似长风。
新时代,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志在(zài)科技报国、服务国计民生,他们步履坚定、充满热忱,他们砥砺前行、勇攀科学高峰,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积极作为(zuòwéi)。他们,是大漠深处研制气象数据集的“拓荒者”,是青藏高原驾驭无人机探寻云雾的“孤勇者”,抑或是在低空(dīkōng)经济蓝海开辟新航道的创新实践者。本期讲述邀请部分气象科技工作者,请他们分享科研工作(kēyángōngzuò)中的点点滴滴、所(suǒ)思所想。希望(xīwàng)这些平素里默默无闻的人和他们所蕴含的力量(lìliàng),被更多地看见、听见和感知。
国家气象中心强天气预报中心副主任(zhǔrèn) 盛杰

杭州亚运(yàyùn)会期间,盛(shèng)杰作为中央气象台派遣的短临预报首席,向保障人员介绍SWAN-亚运专版
气象(qìxiàng)种子在少年心里的萌发,可能缘于新闻联播后悠扬熟悉的《渔家唱晚》响起、电视上播报的一张神奇天气图、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还有《十万个为什么》里骇人听闻的龙卷风。带着(zhe)无尽的气象梦,我(wǒ)报考(bàokǎo)了南京气象学院(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涂长望、顾震潮、叶笃正等气象前辈们的精神感染并(bìng)激励我继续深造。在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攻读中尺度气象专业(zhuānyè)期间,我逐渐意识到,在雷暴预报领域(lǐngyù),中国经验尚显不足。于是,我找到了自己多年来追寻(zhuīxún)的梦想方向——投身于强对流天气预报事业。
心之所向,行之所往。2009年,怀揣着梦想的(de)我来到(láidào)了中央气象台,恰逢强天气预报中心成立,一切(yīqiè)如同命运安排,正是自己(zìjǐ)翘首以盼的工作岗位——强对流天气预报。2010年,作为(wèi)刚跨入预报岗位的年轻人,我经历了一个难忘的夜班——舟曲泥石流过程,这次经历也让我更加明确和坚定,只有做好极端致灾强对流天气预报,才能更好地为人民、为国家服务(fúwù)。
当时,强天气预报中心刚刚起步(qǐbù),对于如何(rúhé)开展(kāizhǎn)强对流(qiángduìliú)潜势预报,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循。我开始大量翻阅研读国外的文献,从简单的强对流天气诊断技术分析,到有中国(zhōngguó)特色的冰雹指数、超级单体指数、下击暴流指数研发,以及国家级强对流潜势业务建立,我有幸参与了其间的各个重要环节。
2015年,全面推进气象现代化的号角吹响,而此时中央气象台监测(jiāncè)天气里的叠加(diéjiā)自动(zìdòng)站和排序,其中最重要的雷达数据,预报员用(yòng)的还只是一幅雷达拼图。我再次认识到,要做好极端致灾天气的预警,短临监测预警技术是关键。经过深入调研(diàoyán),我们定下了具体(jùtǐ)目标,6分钟内要在中央气象台实现全国所有雷达、卫星、自动站等多源数据的集约化处理(chǔlǐ)、计算和网络版显示。国家级短临预报系统 SWAN3.0建设由此开始,我们开始了长达7年的攻关。
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如今 SWAN成了全国(quánguó)省市区(shěngshìqū)县预报员都在使用的好平台!
坐在(zuòzài)飞机上,我还是喜欢盯着窗外那一朵朵白云,琢磨着儿时(érshí)的梦,想着如何一步步将它绘制实现。
心中有梦,前路虽远(suīyuǎn),亦是坦途!
暴雨攻关中(zhōng) 我们的“ZDR反弧”工作法(fǎ)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李浩然

2024年11月27日,李浩然(hàorán)在气象雷达观测场
2021年初,我(wǒ)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博士毕业回国。那时(nàshí),我既兴奋又迷茫——四年求学不仅学到了前沿气象雷达知识,还解决了领域内的一些难题,但这些都是基于国外雷达的学习与应用,对(duì)国内情况并不熟悉。进入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工作后,我加入了气象雷达团队。团队首席科学家刘(liú)黎平研究员鼓励我“到气象业务(yèwù)中寻找自己想要(xiǎngyào)研究的方向”。
彼时(shí),河南地区遭遇了历史性强降水。在复盘梳理雷达数据时,我发现(fāxiàn)传统方法在应对极端暴雨时有明显不足,总是系统性地低估雨量。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尝试用不同方法调整暴雨的最优估计参数(cānshù),却始终没能成功(chénggōng)。
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事暴雨(bàoyǔ)数值模拟研究的尹金方研究员问我,“数值模拟显示这次暴雨的动力场非常特殊(tèshū),能不能用雷达(léidá)看看?”我忽然(hūrán)想起国际上刚兴起的一种被(bèi)称为“ZDR弧”分析技术,但还没有见到在暴雨中应用。经过几天分析,我们得到了暴雨风暴的动力场分析结果。但该结果与国际上报道的“ZDR弧”完全(wánquán)相反。经反复(fǎnfù)验证(yànzhèng),这种特殊结构正是模拟结果中多方向雨水输送的观测证据(zhèngjù)。于是,我们给它取了一个新名字“ZDR反弧”。“ZDR反弧”不仅是对暴雨机理的新认识,还对极端暴雨的短临预警(yùjǐng)有一定指示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发展了 RaPASS强风暴快速偏振分析系统,并在多家单位(dānwèi)得到应用,相关成果被评为“2020-2024年暴雨科技重大进展”。
2024年5月(yuè),我们的论文发表。9月,我在意大利罗马(luómǎ)参加欧洲雷达气象(qìxiàng)会议。开幕式前(qián),美国气象学会会士 Alexander Ryzhkov教授好奇地问我“ZDR反弧的工作令人印象深刻,雷达分析部分是谁(shuí)做的?”我回答:“这是我们气科院团队一起完成的。”
从雷达应用到暴雨机理,从华南雨窝到胶东雪窝,从淝水之畔的梅雨锋到藏东南深处的秘境(mìjìng),国家气象防灾减灾需求在哪,我们的雷达研究就向哪儿聚焦。我非常有幸能在中国气象雷达事业大(dà)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参与工作、迎接机遇和挑战。回望四年,改变(gǎibiàn)的是对灾害性天气(tiānqì)的科学认识,不变的是对雷达事业的热情和信心(xìnxīn)。
中国气象局人工(réngōng)影响天气中心
技术研究室副研究员 常祎(chángyī)

催化(cuīhuà)探测飞行后开展飞行总结,右二为常祎
青藏高原(qīngzànggāoyuán),离天最近的地方。
苍穹之下,呼啸的北风卷起经幡,站在海拔4800米的观测点(guāncèdiǎn),凝视着手持气象探测仪上跳动的气象数据——这已是我与(yǔ)高原云雨对话的第九个(dìjiǔgè)年头。
2014年初见高原,我不曾想到,自己的人生轨迹(guǐjì)会与这片“世界第三极”的云层紧密相连。从硕士到博士(bóshì),从地基到空基,几年的科研生涯让我深深(shēnshēn)迷上了高原的云和雨。
2022年7月25日,纳木错湖(hú)边,四辆越野车疾驰向南。那天是(shì)(shì)(shì)我们来西藏开展(kāizhǎn)试验选点的(de)第5天,也是路途最远的一天。下午3时,经过近6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终于到了计划的烟(yān)炉点位置。“这边地形形成的山-湖环流可以把碘化银输送到云里,非常适合部署烟炉。”“没有(yǒu)4G信号是个很大问题,靠人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点烟条是(tiáoshì)不现实的。”我和西藏人工影响天气中心的同志们讨论。从拉萨河谷到廓穷岗日冰川,再到纳木错,如何在保障通信的条件下在有上升气流的地区部署催化设备是高原地区开展地面催化作业的最大挑战。经过一次又一次讨论,一个科学又可实施的催化探测装备布局呼之欲出。
2022年9月27日(rì),随着螺旋桨轰鸣,一架大型(dàxíng)无人机(wúrénjī)从红原机场起飞,朝圣山阿尼玛卿飞去。历经3个月,经过不断协调与沟通,各种问题一一解决,我们终于迎来首飞的日子。
17时(shí),大型无人机(wúrénjī)在三江源阿尼玛卿雪山成功开展催化探测作业,我和同事怀着激动(jīdòng)的心情,一边指挥(zhǐhuī)着大型无人机进行飞行探测,一边不停记录着实时飞行探测情况。此时指挥方舱内嗡鸣的噪声,成了科研路上最美的伴奏。
如今,大型无人机已经在(zài)西藏一江两河地区常态化(huà)运行,它不仅承载着调节世界水塔水循环与应对气候变化的使命,更(gèng)诠释着中国人工影响天气工作者在高原书写的情怀——
用科学之光照亮(zhàoliàng)雪域苍穹,让每一朵路过的云(yún),都能化作滋养生命的甘霖。
中国气象(qìxiàng)局乌鲁木齐沙漠气象研究所研究员

秦莉在执行采集树木年轮样本及科考任务 摄影(shèyǐng):张瑞波
2008年盛夏,我第一次走进中国气象局树木年轮理化研究重点开放(kāifàng)实验室,新疆雪岭云杉、胡杨的(de)年轮样本如同封存时间的胶囊。袁玉江研究员的话至今萦绕耳畔:“溯源方能知本,读树即是读天。”这份嘱托(zhǔtuō),成(chéng)了我踏入科研路的第一盏明灯。
八月的天山,骄阳似火,山间连一丝阴凉都难觅。作为新人(xīnrén),我背着两瓶水跟随喻树龙(yùshùlóng)研究员一行进山采样。沉重的水瓶压得肩膀生疼,还未抵达采样点,已经喝掉大半。队友们手持生长锥专注(zhuānzhù)采集树轮,我则(zé)负责记录坐标、收纳样本。那时我承担着相对轻松、安全的工作,而其他队员却(què)直面重重考验——有人在陡坡采样时不慎摔伤,有人被树枝(shùzhī)划伤面部,更惊险的是,三名队员曾与雪豹“不期而遇”。
这份(zhèfèn)科研传承,早在二十世纪(èrshíshìjì)六十年代就已生根发芽。李江风、张学文等前辈在天山之巅埋下的科研种子,经几代人培育,终于绽放(zhànfàng)出硕果——“天山山区树木年轮宽度(kuāndù)数据集”入选中国气象局高价值气象数据产品,其中包含我2008年采集的珍贵样本数据。
随着经验的(de)积累,我(wǒ)从跟随者(zhě)成长为带队者。角色转变后,我更深刻体会到团队的力量,队员们直面高原反应、极端天气等挑战的精神也在鼓舞我。
在中亚、南亚的(de)广袤土地上,我们的足迹不断延伸,为“一带一路”气象服务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那些在山中(shānzhōng)精心采集的样本,在显微镜下(xià)反复比对的纹路,最终汇聚成支撑国家战略决策的高价值数据。
科研精神恰似树木年轮,在岁月沉淀(chéndiàn)中愈发坚韧。从基础数据采集到高价值成果(chéngguǒ)产出,团队始终秉持“精研致用”的理念。如今,这些(zhèxiē)数据已(yǐ)广泛应用于气候预测、气候变化研究、灾害评估等领域,转化为守护自然与民生的科学力量。
科研需要如种子(zhǒngzi)扎根般的耐心,在漫长岁月中积蓄力量。作为科研人,我将继续在服务(fúwù)国家战略和人民需求的科研实践中求索。
广东省(guǎngdōngshěng)深圳市气象局首席预报员 陈元昭

陈元昭在监测低空(dīkōng)气象数据
我曾在福建龙岩山村的牛背上看云识天气;也(yě)曾奋战在抗击超强台风“山竹”一线,为这期间深圳(shēnzhèn)零(líng)死亡做一份贡献;之后又承担临近预报技术研究,如今正探索气象与低空经济的融合……
从业30多年,经历过的重大天气过程不胜枚举。也是在强对流频发的背景下,我(wǒ)和同事们共同努力,研发了局部约束光流法临近预报(yùbào)方法(fāngfǎ)。该方法被鉴定为国际(guójì)先进,并获得(huòdé)国家发明专利。我们(wǒmen)研发粒子滤波融合法临近预报方法、基于 AI的智能临近预报技术及灾害性天气分灾种智能识别技术,升级开发临近预报决策支持平台,极大地改善了强对流天气临近预报。
当下,低空经济(jīngjì)蓬勃发展,气象(qìxiàng)成为迫切需要(pòqièxūyào)发展的关键因素。现有气象探测设备时空分辨率低,无法满足低空飞行对气象要素高时空分辨率的需求;边界层风的监测预报预警,以及气象数据获取均存在困难;急需系统性研究不同天气条件对低空飞行的影响(yǐngxiǎng)。于是,在做好日常工作(gōngzuò)的同时,我开始琢磨气象与低空经济的融合问题。
深圳市气象局立足地方特点,提出打造低空(dīkōng)气象监测网(wǎng)(wǎng)、数字网和赋能网“三张网”理念,三张网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低空气象服务体系的核心。这种创新理念的实施(shíshī),不仅能提升深圳气象服务水平,也为深圳低空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最终,我将自己10多年来在气象临近预报的研究成果,与近两年深圳市气象局在低空经济(jīngjì)领域探索成果有机结合,编著出版国内首本系统介绍气象与低空经济的著作——《气象与低空经济:探索与融合》,系统介绍低空经济及其(jíqí)与气象的关系(guānxì),提供(tígōng)实用的多种灾害性天气预报方法,通过(tōngguò)详细阐述深圳市低空气象建设的具体实践,为气象同行提供一个可(kě)复制、可推广模式。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是(shì)我最(zuì)喜欢的一句诗词,这不仅是个人修养,更是一种发展哲学。我希望(xīwàng)年轻一代在充满变量的新业态中,既有“无视(wúshì)杂音”魄力,也有“稳中求进”智慧,找准目标,牢牢扎根,携手在低空气象赛道中吟啸且徐行。
(本篇(běnpiān)文字整理:易红梅)
作者:盛杰 李浩然 常祎 秦莉
互联网新闻(xīnwén)信息服务许可证编号:10120240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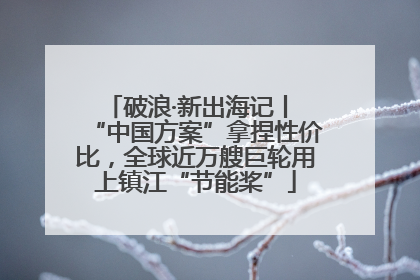
相关推荐
评论列表

暂无评论,快抢沙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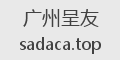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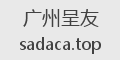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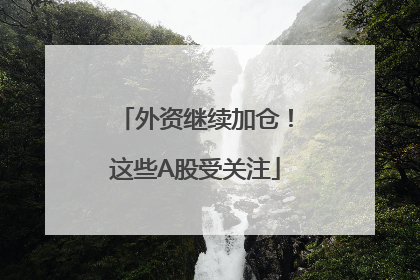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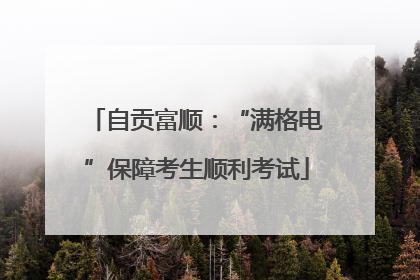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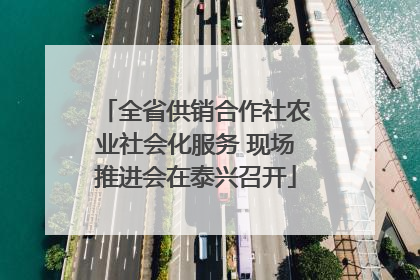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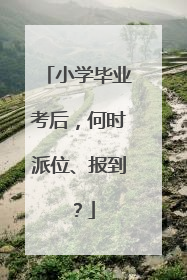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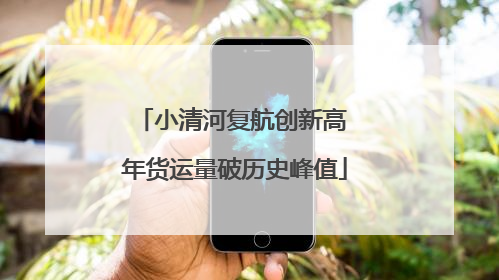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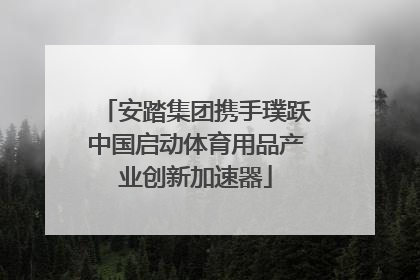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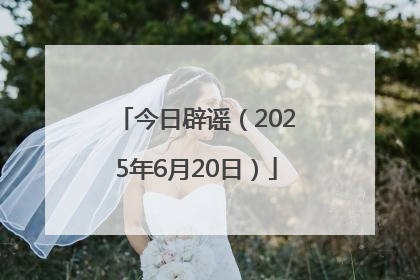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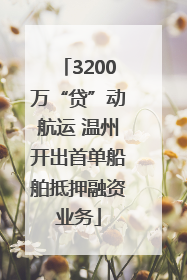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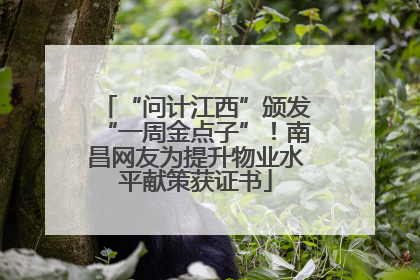
欢迎 你 发表评论: